“谣言”这个词的褒贬,在学者看来没有我们日常以为的那么简单,它不仅是“虚假的信息”“不实的言论”。谣言的流传有真有假,最终结果或者证伪,或者证真,所以其本质特点是“未经证实”。作者就此“带我们闯入谣言规律的核心,从根本上进入信仰的领域”。
1950年代,好莱坞演员詹姆斯·迪恩因主演了《天伦梦觉》《无因的反叛》及《巨人》等极具号召力的作品成为巨星。他的照片反复印在大小海报上,可口可乐,Levi’s牛仔裤,Zippo打火机,连老牌的老鹰乐队都把他写成歌曲。电影、照片,乃至真实中的詹姆斯·迪恩成为当年青年反叛象征的符号,如今却和玛莉莲·梦露、猫王及Levi’s牛仔裤一起,成为美国文化的象征,成为一代传奇。
然而,1955年9月30日,在加利福尼亚,酷爱跑车运动的詹姆斯·迪恩以每小时160公里的车速飙车时不幸发生车祸死亡。然而,偶像是不死的,他死后50年中人们不断传播着各种谣言。据传,他被车祸毁容,因此一直隐居在洛杉矶附近的农庄里;他驾驶的那辆车的残骸,被维修此车的工人买了去,但是当车从卡车上卸下时,车闸松动,一名旁观者的双腿被压断;肇事车的发动机被一位发动机的狂热收集者亨利买走,但不久之后亨利就在比赛中受了重伤……
最奇特的是,车祸之后,詹姆斯·迪恩驾驶的那辆车的车身被运往他那天要去的城市途中,运送卡车刹车时把车身甩了出去,砸死了一个人,引发了连环撞车事故。最后,车祸13年后,这辆神奇的车不翼而飞,似乎被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带离了尘世。
人们只相信自己相信的,相信自己的愿望,于是谣言带着这些愿望四处游走,不息不死。
詹姆斯·迪恩已经死了不是吗?沃尔特·李普曼在《舆论》中说:“成见系统一旦完全固定下来,我们的注意力就会受到支持这一系统的事实的吸引,对于和它相抵触的事实则会视而不见。大概是因为那些事实跟它一拍即合,所以,善良的人们总能为善良找出无数理由,邪恶的人们也总能为邪恶找出无数理由。”
我们都熟悉这样的实验或游戏:十个人排成一排,第一个人向第二个人说一句话,让第二个人向第三个人转述,最终转到最后一个人时,原话及其原意很可能已经丢失。出于追求时效性和方便传播的目的,语言被简化缩略,在反复流通中会有太多的增添和丢失,以致面目全非,成为“事实的碎片”。
上升到政治层面,李普曼质疑传统民主理论所崇拜的“公众”,他认为公众只是一个“幻影”,“大部分参与的公众,对事情并无充分的了解,甚至也没有兴趣了解。他们唯一能够做的,就是……表达最强烈的反抗情绪……实在无法使自己保持清醒”。他可能只看到自己想看的,如果看不到,他会用想象来补充。所以,毫不奇怪的是,选举期间就是谣言的高发期。
谣言的恐怖与浪漫的想象
谣言伴随着的想象可能是浪漫的,也可能是可怖的。
众口铄金,积毁销骨,这是谣言的最极端形式。丹麦电影《狩猎》可以提供这方面的最佳案例。影片中,一个名叫卡拉的小女孩生活在父母对她缺乏关爱与管教的家庭,她不免把感情转移到从事幼儿教育的男主角卢卡斯身上。她对卢卡斯萌生出一种朦胧的感情,一种类似父爱的温情。她根本分辨不清这种微妙的情感,她极力想表达这种情感,送礼物给卢卡斯的时候却遭到拒绝。对她而言,犹如从父母那里索爱而不得——这才导致了一个谎言的开始,一个悲剧的开端。
这个谎言是卡拉说出来的,目的是诋毁卢卡斯。卡拉报复性的谎言让卢卡斯背负起了性侵女童的罪名,一时间,所有的人都愤怒了。从幼儿园园长开始,到家长,再到镇里的每一个人;从单独谈话,到通知并警告家长,再到报警让警方介入,一切在人们眼中都合情合理。每个人都自我陶醉在他们所认为的“正义感”中,不能自拔。于是,卢卡斯这个曾经的好好先生,成了整个小镇排挤和压迫的对象,好友的愤怒,前妻的不信任,爱犬的死亡和陌生人的恶意等等,最终让卢卡斯几近崩溃。
这起事件中,没有人眼睛是“雪亮”的。所谓的“真相”,是幼儿园大妈想象出来的恶心画面,是谣言一次次传播的添油加醋,是昔日朋友的不容分辩,是无关路人的拳脚相加,是最后的枪声响起。
公众舆论完成了对一个人的审判,并彻底毁灭了一个人。影评人木卫二曾经写道:为何一个平静而有秩序的社会,会让一个如此之轻的谎言,引发如此严厉的惩罚。而在如今的网络世界里,为什么仅凭一段文字、几张图片,所有人都相信,他们比其他人更靠近真相,更有责任和义务行使人身攻击口诛笔伐之实。往更糟糕的层面去想,所谓的善与恶、白与黑,多数人是根本分不清的,也可能根本是与他们的切身生活无关紧要——无论过去现在或者是将来,这是多么悲观的情景!因为,总有一天,枪口掉转,你自己也许就会成为下一个猎物。
从这个角度,就不难理解李普曼何以对舆论抱着深深的怀疑。他的另一部著作《幻影公众》写作之时正是“一战”后不久。1917年,美国介入“一战”,国会以惊人的速度一致通过了《反间谍法》和《反煽动叛乱法》,如果有人阻挠政府发行战争债券,阻拦征兵,就会被诉诸法律。而这一切,都得到了大多数民众的支持,并深深影响了后来的越战、伊拉克战争、阿富汗战争。李普曼说:“……凡此种种都构成了一个恐怖的君主统治,在这个统治下,不允许有诚实正直的思想,不支持温和节制的做法,疯狂取代了理性。”舆论会被裹挟,罔顾是非黑白。
古斯塔夫·勒庞在《乌合之众》中说得明白:“孤立的个人很清楚,在孤身一人时,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……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,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,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。”人类的肌体的确能够产生大量狂热的激情,这股激情摧枯拉朽,既可能荡涤邪恶,也可能滥杀无辜。
为了达到目的,“一些可以轻易在群体中流传的‘神话’就可以产生,不仅是因为他们极端轻信,也是事件在人群的想象中经过奇妙曲解之后造成的后果。在群体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最简单的事情,不久就会变得面目全非,把歪曲性的想像力所引起的幻觉和真实事件混为一谈。”
《谣言:世界最古老的传媒》中所举的例子,包括宝洁公司的徽标,徽标上绘有罗马神话中主神朱庇特老人的侧像,侧像呈弯月形。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,谣言开始对这一徽标进行猛烈的攻击:徽标暗指月亮派及其创始人的反基督化身,图案上的星星可以勾画出数字“666”,那是撒旦的标志。一波一波的谣言,欲置公司于死地。“然而,该标志自从这个完全清教徒式的公司创建以来就出现了,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”。
1985年4月,不堪其扰的宝洁公司,不得不在所有产品上取消了这个徽标。
谣言的传染与真相的缺失
德国政治学家、传播学者伊丽莎白·诺尔·诺依曼于1980年出版《沉默的螺旋:舆论——我们的社会皮肤》一书,进一步完善了“沉默的螺旋”理论。或许诺伊曼女士自己也没料到,这个模型理论会在整个人类传播学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时至今日,身处互联网世界的我们,也会被这一“螺旋”所影响。诺依曼“沉默的螺旋”包含了这样一个命题:大众传播通过营造“意见环境”来影响和制约舆论。
诺依曼在书的前言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:在意大利的某个小镇,那里世世代代居住着忠厚的百姓,还有声望卓著的伯爵及伯爵夫人。在城镇外山上的古堡里,住着一个怪人,他那些出格的做法一直令城里人很生气。一天,这个怪人赶着一头独角兽。人们看到后,纷纷摇头。过了一会儿,人们看到伯爵和伯爵夫人也赶着一头独角兽。这却成了一个信号,那就是全城的人都应该有一头独角兽。之后那个怪人陆续带来了蛇发女妖、人头狮身龙尾兽,开始所有的人都被吓坏了,但是,当伯爵和伯爵夫人也这么做时,这种行为又成了潮流……
启蒙主义哲学家约翰·洛克曾说,权威的主宰,时尚中的规则和陋习,被引导的公众意见,这些东西要比任何一条宗教戒律或法规更为个人所遵循。于是,独角兽、蛇发女妖、龙尾怪兽,都可能变成时尚,变成狂热的追求,变成了不顾一切地盲从。诺依曼将李普曼的“刻板成见”理论引入自己的观察中,认为“刻板成见”是“意见气候”中的积雨云,社会成员体察“意见气候”并作出趋同行为。
在《谣言:世界最古老的传媒》中,作者揭示了人类的好奇心以及由好奇心带来的各种谣言的传播,“那些消费量很大的产品市场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谣言生产场域”。1984年,法国推出第一款液体洗衣剂,大量的消费者使用它,但此后关于洗衣剂“洗出来的内衣有一个个大洞”的谣言甚嚣尘上。即便所有传谣的人用这款洗衣剂,并且没有人“洗出来的内衣有一个个大洞”,都是道听途说。
其他类似的谣言包含了含氟牙膏、不粘锅、茴香酒、隐形眼镜——谣言说隐形眼镜会致盲。很多人试图保留他们过去的消费习惯,用谣言来使自己拒绝变革的行为合法化,并且攻击他们熟悉的世界被科学和技术所统治。
而另一方面,谣言销售学也随之兴起。1984年,马赛大磨坊面包公司推出一款新式法棍面包。公司本来想在电视上大肆进行广告宣传,后因预算不足而取消,其竞争对手造谣暗示新式面包销售不畅。某些公司夸大产品或服务的作用,也用上了制造谣言的手段,类似于我们曾熟知的“打鸡血”“气功识字”,类似于一些影视公司用“非常手段”推销自己的产品……
谣言往往是想象的产物,这种想象或者因为美好的愿望,或者因为卑劣的动机;舆论的狂潮会加速谣言的传播,会裹挟不明真相的人们产生狂热的情绪,而谣言的制造者也往往是狂热之徒。甚至,一些历史学家为了得出想要的结论,也不惜歪曲或篡改历史,或者使用不可靠的文献资料,而且用传说代替史实,甚至恶意掩盖历史真相。
阿马蒂亚·森在《身份与暴力》中说:“在一个联系紧密的社区中,居民们可以本能地抱有团体精神;但在另一方面,他们也可以向刚从他处迁入的移民家中扔砖头。”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·森在这部包罗万象的著作中认为,驱使着这些行动的,不仅仅是那些不可解脱的仇恨,还有让人们罔顾真相和常识的思想混乱,而这正是谣言滋生的土壤。
如果谣言犹如冰雪,那么唯有真相犹如阳光,可以让冰雪消融。
转载请注明来自易保微信测试平台,本文标题:《谣言如冰雪,真相如阳光 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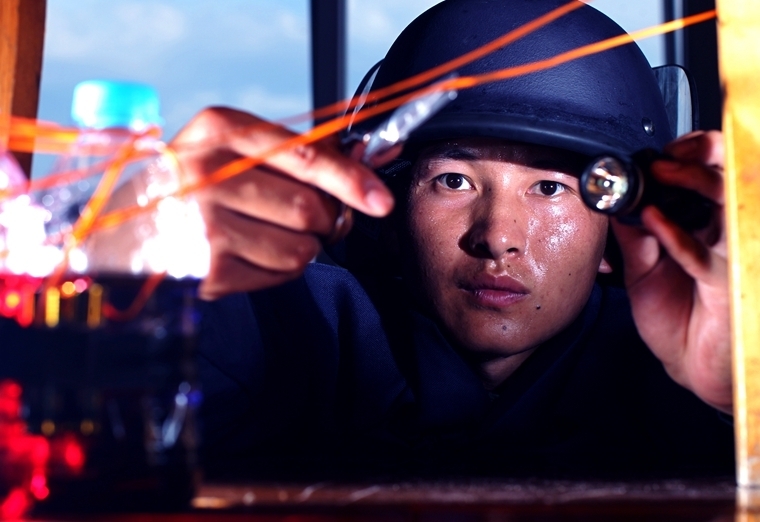








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
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